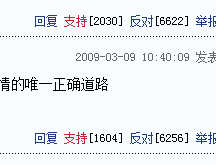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记得这个标题的出处,如果你记得,不妨举个手。很美好的童年回忆:),其实连我都忘记了具体细节(除了那个忘了修电梯的一千层的少年宫),今天想起这个动画片完全是因为一本书的名字。不过感谢互联网所赐,这种类似abandonware的动画片居然也能够在优酷找到。今天就趁做作业休息时间又重温了一遍。
现在都说中国动画片不行,但这很显然不是天生的。像没头脑和不高兴,还有些更近一点的黑猫警长,神笔马良,邋遢大王等动画片,把他们的画面稍微翻新一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照样是佳作。而我在这里通过CCTV4看到的动画片,几乎是一个都没印象(不过他们现在还在放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我连名字都叫不出,只记得某次一个长得很奇怪的阿姨在冰天雪地里教儿子走路要做记号,不然会走到原地。
这是知识没错,但这是儿童需要的知识么?这是中国人一个老毛病,倒不仅仅是动画片,任何一件事情必须要“有意义”才价值,这个“意义”包括经济价值和政治正确的意义,却不包括做人本身的意义,也不包括娱乐的意义,例如让自己开怀大笑一下。
如果非要给那些不该有“意义”的事情加上些“意义”,那最后的结果很显然,就会成为四不象。相声不能针砭时弊,那只能想法设法搞恶俗逗人发笑;而动画片,我认为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让未成年人(其实成年人也如此,例如The Simpsons)通过轻松,幽默方式来提前接触外面的现实社会,让他们知道他们将会遇见什么,学习如何如生存和面对现实的能力。如果老是往里面灌那些“意义”,看上去当然让人了然无味甚至觉得厌恶。想想我们小时候多好呀,一堆优秀的国产动画,也能看到例如蓝精灵之类的外国动画,而且通常还寓教于乐。哪像现在,小孩看个动画片也要讲政治正确,为了搞“国产动画”,让一群思维被束缚的艺术家们抄袭欧美动画。
不高兴和没头脑就是很多人都有的毛病,包括我在内,所以我从《没头脑和不高兴》学到的第一点就是不能做没头脑和不高兴。这对我来说一直都有现实意义,我是一个很马虎的人,实际上现在也是如此,你如果是这个blog的常客而且“认真”读完了我的blog,你多半会同意这一点。虽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语言能力障碍的问题,但主要的问题还是马虎,我虽然会检查文章语句通顺问题,但那通常是三天之后的事情。但小时候就更夸张,我的头脑基本上是“木”的,反应不仅慢拍而且还常常做错事,没头脑那种在画上写反自己名字的行为,悄悄告诉你,我偶尔也会犯:)
而至于不高兴,一个小孩通常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耍性子,以自我为中心是不对的。但不高兴这个人物却能将这一点通过比较轻松的方式展示出来,成功地用小朋友的语言阐述一个简单,受众却很难理解的道理。
我个人相信这个动画原本是要教育小孩的,反正当时我是被震惊了,很多小孩都有“长大了我就不乱来了”之类的想法,也包括我在内,因此才能对名字有那么深的印象。但艺术来源于生活,我相信这部源自80年代的动画片,原型上是能找到成人的影子的,特别是长大之后的没头脑和不高兴:
没头脑长大之后成了总建筑设计师,但老毛病还在,再多的客观现实也无法让他改正丢三落四,不负责任,自以为是等坏习惯。不过当在自己设计的,没有电梯999层高楼面前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没头脑时,却一直不敢承认,毕竟楼都建起来了。可是,第999层的演出是如此的遥远,要爬一个月,没头脑没有干粮,也没有被窝,知道自己是爬不上去的,可是就有一群善良得天真的小朋友愿意分享装备,于是没头脑就勉强被推搡着往上爬了。不过没头脑毕竟长大了,不如小朋友的体力好,还有5层楼的时候终于爬不动了,最后勉强依靠小朋友设计的一个简易电梯到了999层去看戏。
不高兴长大之后成了一名演员。在戏台上演的明明是老虎,却不愿意被武松打,更不愿意躺在台上装死,那得让不高兴多窝囊,多不高兴啊。不高兴和武松大战八百回合之后,冲出了舞台,见人就追,因为他“不高兴”。不高兴最后盯上了没头脑,扭打成了一团,打到楼梯口,没头脑好不容易才爬上999层,结果两个人瞬间从999层滚回到了起点。
不知道你对这两个人物有什么看法。作为一名成人再回去看这个动画片,我倒是有一些新的感想。不高兴和没头脑都会产生危害,但他们俩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没头脑比较容易控制,你可以把他晾在一边,没有电梯的999层高楼你不进去就是了,或者可以要他提供电梯;但不高兴在哪里都会成为问题,因为不高兴是不需要理由也是不分场合的,无论做什么事,永远都有不高兴的理由,总设计师的危害就限于没有做好他的工作,而不高兴,会先在999层楼上搭一个台子,画个大饼让你去爬楼,而且无论你把他放到哪个位置上,都会产生相当大的破坏力。
《没头脑和不高兴》动画虽然是80年代的,但其实是源自于任溶溶50年代的一篇同名儿童文学。老人家似乎还健在,先祝福一下。再来看看他讲述《没头脑和不高兴》文章的创作经历:
有读者问,《没头脑和不高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任溶溶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自己就是‘没头脑’,小孩子么,都是‘不高兴’呀。天冷了,早上家长让小朋友多穿衣服,往往得来一句‘不高兴’。文学是生活中来的。”
“不高兴”虽然更接近于“小孩子”的行为,但任溶溶依然告诫了家长:
“千万不要骗小孩子,他会记住的。”
当然,这篇blog和我的其他文章一样,其背后多半都有一些其他的含义。我不知道这算是影评,还是在冒充书评(毕竟我还没读过那本书),但无论你是看动画的还是看书的,我都希望你可千万不要做那个叫“不高兴”的小孩,无论碰到什么事都是那同一句台词:
不高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