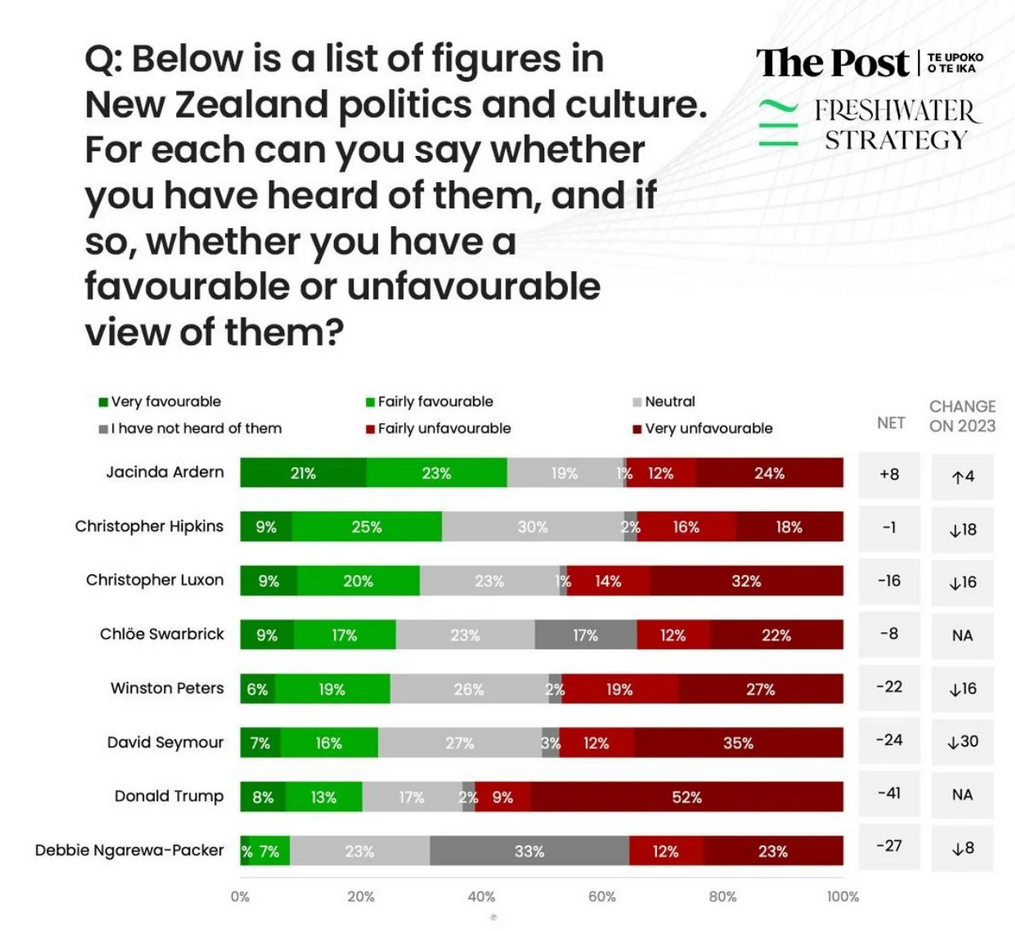当Dirty Politics 一书消息走漏时,不少人认为书中内容可能是斯诺登泄露的新西兰情报网络。虽然并非如此,但事实依然出乎意料。
出版后我花最快时间通读了一遍,唯一感觉并非是对书中的内容感到吃惊,而是——新西兰政界怎么可能有这么邪恶的一群人?我知道邪恶一词听上去似乎很夸张,但相信我,我找不出第二个词。为了政治和金钱私利,他人的隐私、权利、家庭到个人及国家利益和安全,都是政治棋盘上的筹码而已。一些行为,比如私自进入反对党电脑系统,和为了政治私利解密和使用机密文件,已经有触法嫌疑。
本书作者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中唯一的新西兰成员。如果还记得的话,该组织曾经公布过和中国极为相关的海外离岸账户资料。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他的政治观点,但作为全球披露美国情报网络的先驱者,至2002年毁掉工党政府议席过半的梦想,从没有人能成功把他打成荒谬的阴谋论者。这次他书中引用的email中倒是提到了一种中国人,这种人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这家伙让好多中国富豪的资料泄露了,中国人丢了脸之后会很暴力,也许我们应该把他的住址泄露给中国【朋友】。”
至于斯诺登对新西兰情报网络的爆料,现在看上去不得不说确实缺少实证。但还是那句话,不管人们喜不喜欢斯诺登的所作所为,从没有人能证明他无意或者有意撒谎。而我在中文广播里听到的最大笑话就是:“John Key 有道德洁癖”。
要我列出他的每条谎言和相关链接,得需要我一个星期全职投入。但斯诺登和记者Greenwald 所揭露出的最重要一点,无疑是2013年8月在通过GCSB修改法案时,John Key故意误导了全国公众,并且在当时信誓旦旦的宣称,“如果GCSB进行任何大面积监控,我就下台”。 发布会提供的不多证据显示,修改法案的唯一目的,就是将大面积监控合法化。而前GCSB负责人能给出的最好说法是,光是收集每个人都信息不算“surveillance”,一定要有人在读每一个人的邮件才算。
如果大部分人只关心经济问题,那么,不知有多少选民注意到,John Key 在选举辩论中,不加思考的直接把对自己不利的统计局数据称为“谎言”;或者无法回答自己政策的开销是如何算出来的;或者,将负债累累称颂为一项政绩。
不管是肮脏政治还是情报收集,有人也许会说,政治就是如此,政客的天性就是说谎。这也许是事实,但我难以理解的是,面对John Key 的笑脸,公众能如此轻松的对所有谎言照单全收。当去年GCSB法案进行讨论时,任何看过法案的人都知道这事不能再明了:原来的法律中明文禁止对新西兰人和永久居民进行任何程度的监控,而修改案将这一条保护添加各种例外。而民众却认为,这个修法不重要,相信总理就好?
不用dirty politics 一书提醒大家,已经很明显的一件事是,现任政府正在有意或无意地改造新西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新西兰本为全世界最为进步主义的国家之一。我就不列举那些左翼分子最爱说的种种新西兰成就了,但这些成就之所以能达到,和一个公开、民主、自由的社会是分不开的。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不仅能自由获取信息和参与到公众辩论中,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对社会中的方方面面都有责任去了解,思考和参与——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新西兰都是西方国家中大选投票率名列前茅的国家,常常超过85%甚至90%。
而今天,这种政治传统正面临着危机。人们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事实只有一个。不过,在过去三年的public discourse中,看到的更多是美式选举策略。领袖永远是一尘不染,诚实可靠,值得信赖的人。而作为天朝人,对种种贴标签的行为更是再熟悉不过了:国家党=光明未来;工党=乱花钱;外国记者=Dotcom爪牙。虽然这些标签通常都没有附带以事实为依据的解释,但是让一个值得信赖的领袖不断重复这些“事实”,那当然就是真的了。加之于这种人通常都是影帝,逼真度就又提高了一级。
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不可能每人都有自己版本的事实。在公共领域的任何讨论,都需有事实的最大化作为前提,intelligent debate 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公共领域辩论被庸俗简化的趋势都在,但很少看到书中所介绍的那样,背后推手有意识的通过操纵、控制、误导等手段来鼓励这一点。
众多不同观点是民主常态。但是,这个社会正在逐渐遗忘的一点是,不管人们支持哪个政党,在具体到每一个单独事务上,最终做决定的,必须还是得人们自己。但是,当社会中出现“我把决定权交给某某党或者某某人,他们的决定一定是最好的”这种思维定势时,最终结果都不会太好看。Homer Simpson 所来自的那个国度,“选举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我们用不着自己思考”,最终结果只能是大众普遍对政治和社会议题失去兴趣。而除了政客和既得利益集团得利,其他所有人都将会变成输家。
作为一个小国家,重要决定交付民众是新西兰的一项长期政治传统。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比例代表制。当人们讨论比例代表制的种种“坏处”之时,却很少有人提及当年为什么会引入这个制度——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工党和国家党都引入了在当时的人看起来,十分极端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改造计划。而两个党做这些事之前,都没有获得社会广泛同意。新西兰人看到了一党独大的坏处,并在当年积极通过社会活动改变现实。
而这个国家的另一个传统则是,众人之事就是自己的事,而这传统可以从殖民地历史中找到。在当时,毛利人权利问题就是导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被分为两块殖民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哪怕是在土地战争之后,毛利人也被称为“智商高于澳大利亚土著”,获得了在澳大利亚的投票权。
国家党的高支持率最早源自2004年的Orewa Speech。这是一个重要分界线,之前国家党的支持率都是在27%左右徘徊。在之后就长期保持在40%以上。对毛利人,岛民究竟是不是混吃混喝,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同意大部分华人的看法。但是,一个以种族问题拉升选票的政党,无论他的得票率是5%还是45%,反华人还是反其他人,都是需要警惕的。(题外话:这一部分的故事在Hager的另一本书, The Hollow Men中重点提及)
这个道理很简单,今天为了各种原因而打种族牌,你也许会认为对你有利而强烈支持。但是,明天要是出现一群比你更有钱的人;另一个政党依样画瓢也想要提高支持率;或者仅仅是上一个目标消失,需要找新敌人,那到时候被清理的就是你。这都不需要我列证据,看看一些政党,例如保守党在这次选举中的表现就知道了。
如果你是拥有选举权的华人,我希望你能考虑这个问题:你如果准备在这个国家扎根安家,终老一生,你觉得为了一个星期几杯咖啡到一顿饭的钱(看你这顿饭有多贵),培养出如此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真的是你的长期利益所在吗?要知道,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永远胜利,你也无法保证下一个金牌影帝的政治观点就和你相同。
当然,如果你是类似于刘阳之类的卷了钱跑出来,或者纯粹是捞一把就跑的炒房客(我知道很多是洗钱的),这明显不是一个考虑范畴,反正赚到钱就好。
一个恨人有笑人无的社会、一个别人过得不好自己就开心的社会,绝对不是新西兰的传统,也不应该是新西兰的未来。我为什么痛恨这种社会,原因很简单:我就来自于这样的社会。如果有华人选民有耐心看到最后一句,那么不妨再试试把所有和新西兰相关的描述换成祖国,会发现我这随便乱写的一点东西还是能读通。而我,绝不希望这个国家成为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