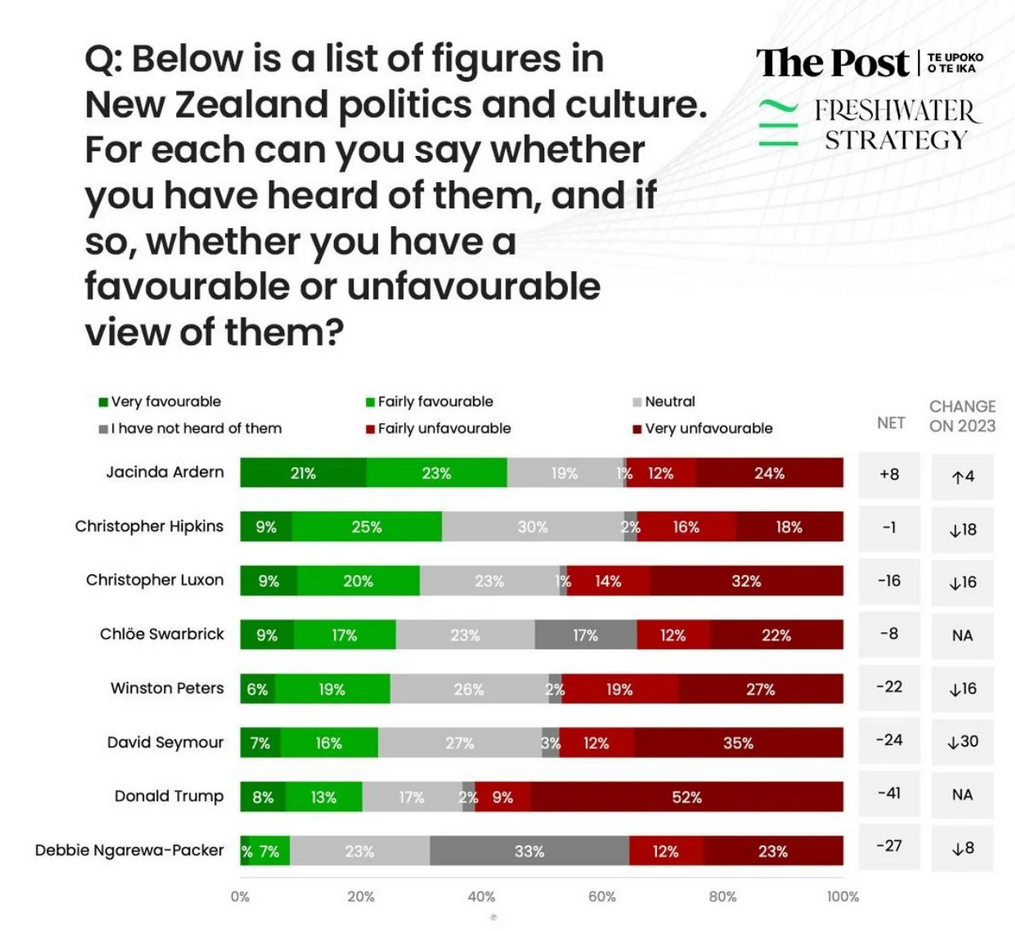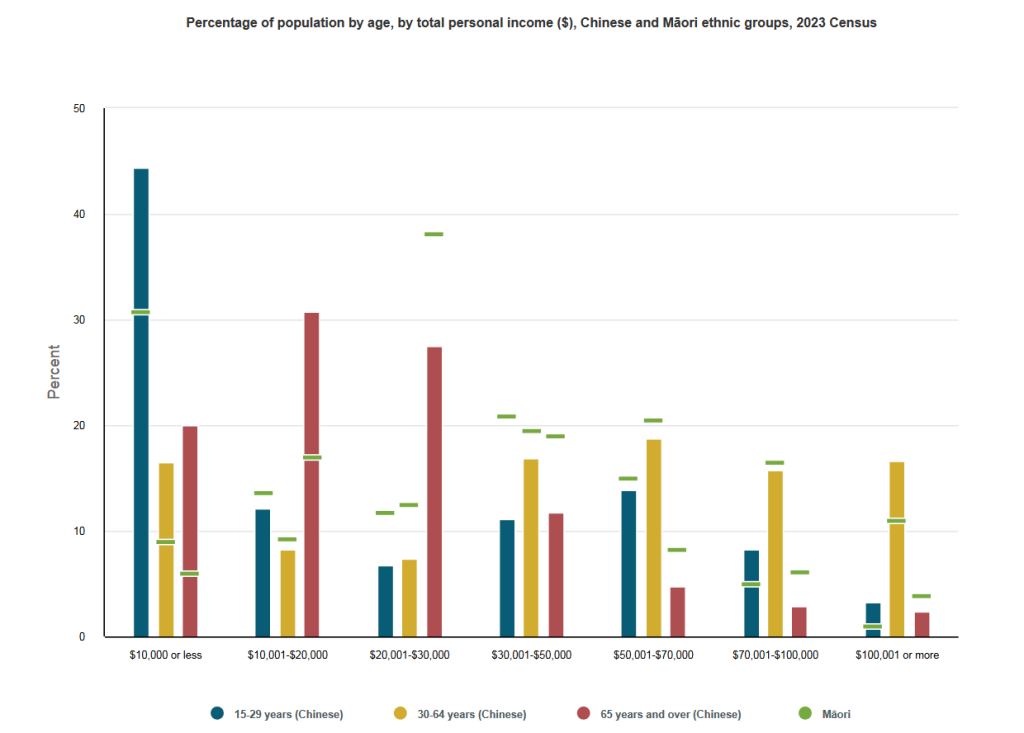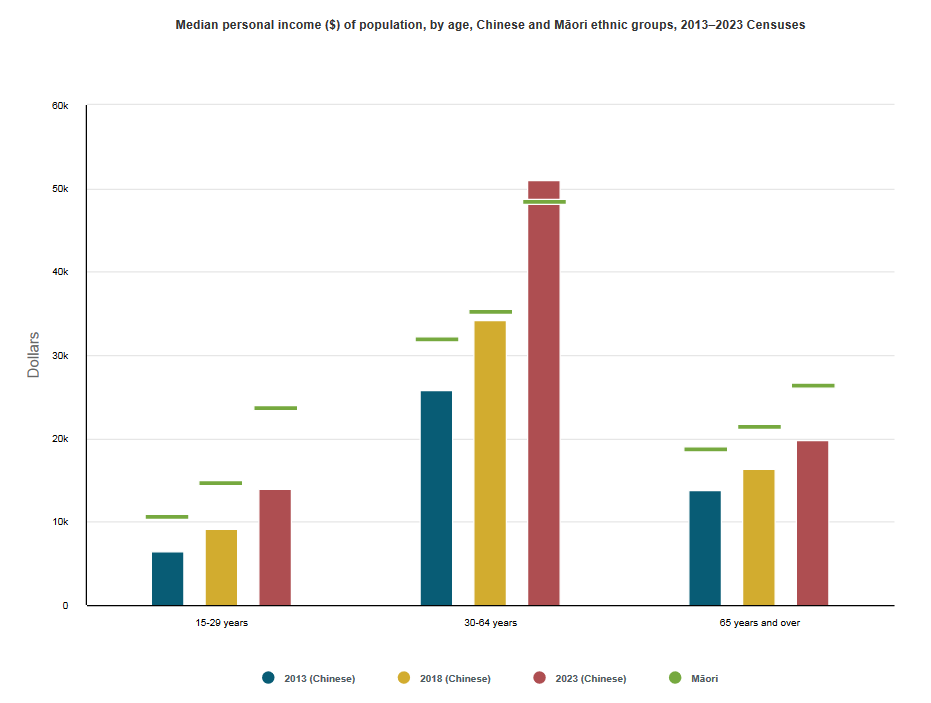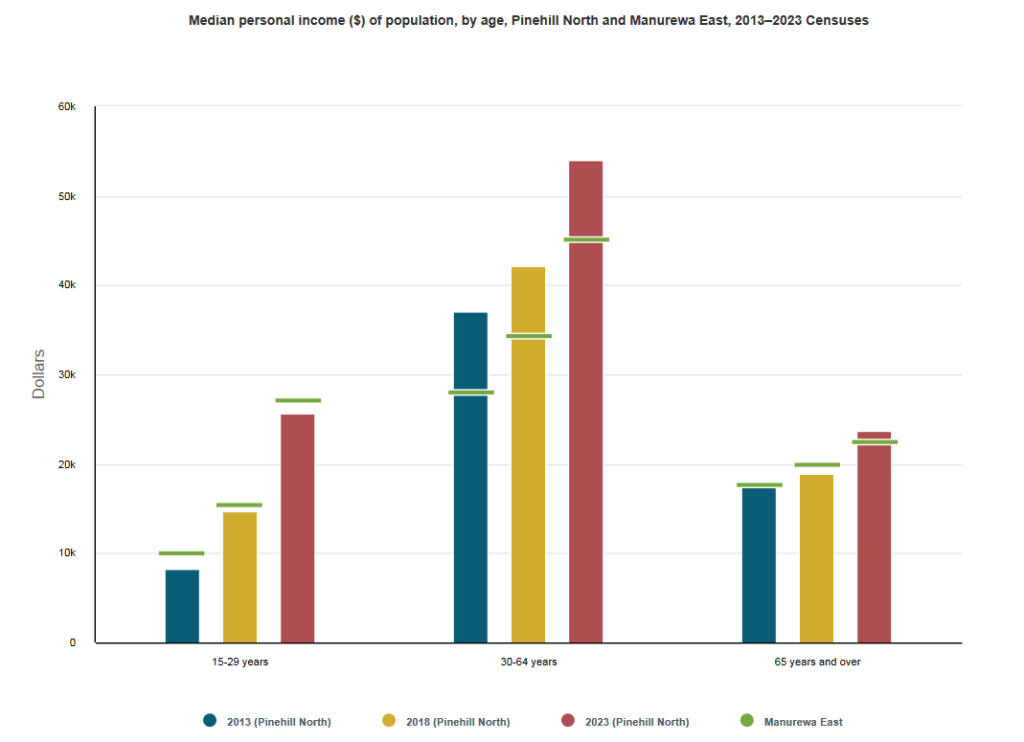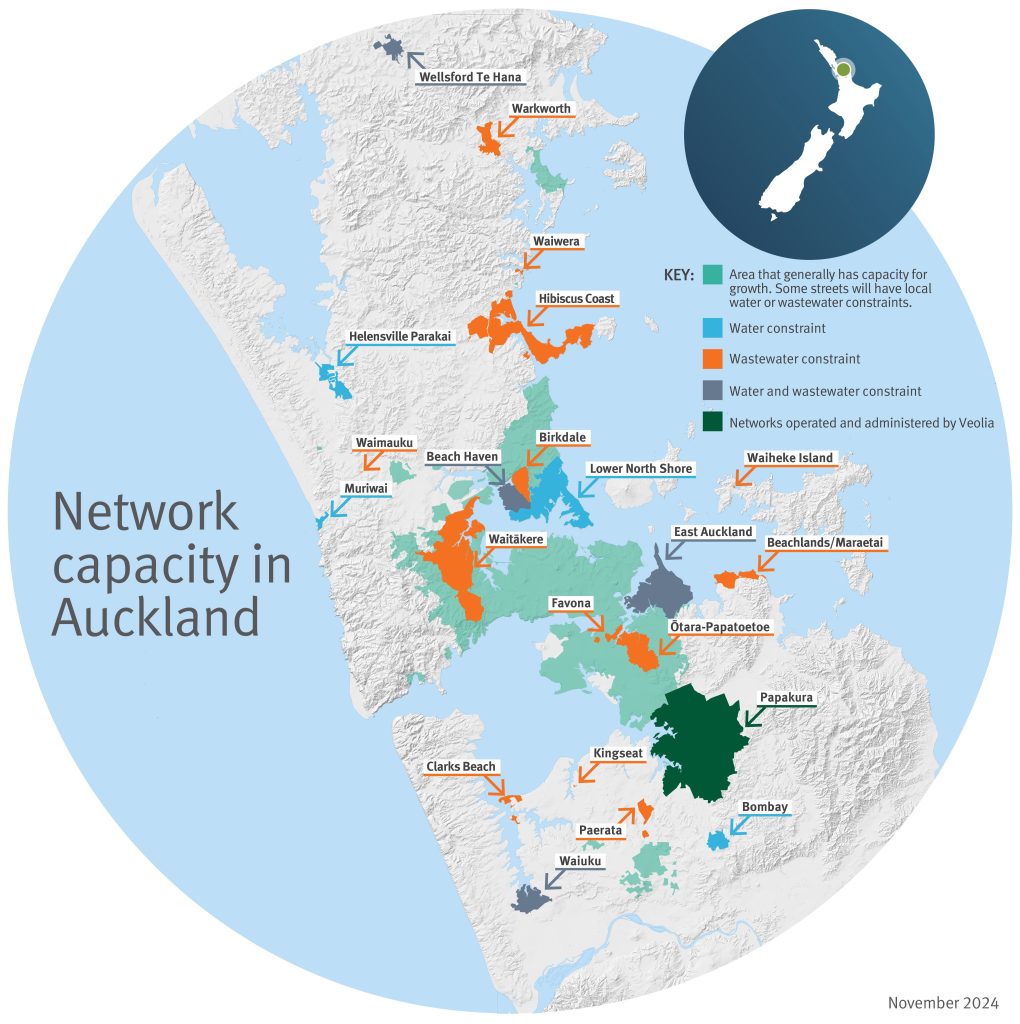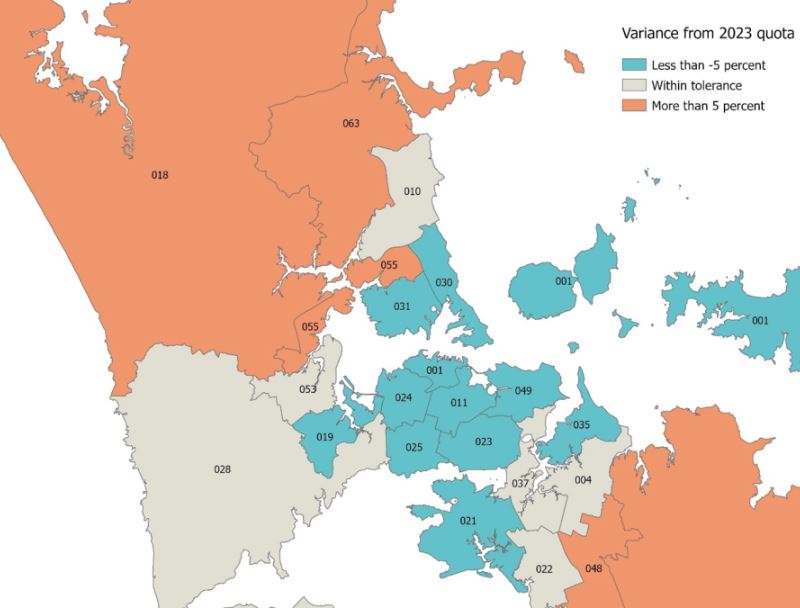The Spinoff 网站上有一个长期连载栏目,’the cost of being’,刊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成本以及他们对现状的看法。我时不时就想起看几篇,毕竟比起统计局的数字要生动太多了。而另一方面,每一个人对生活追求也不同。有些看着生活成本非常紧凑的人,自我评价是还“过得去”,而一些收入明显前10-20%的家庭却觉得马上就要崩盘了。生活成本单用数字来比没有意义,而且如果不能正确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则很可能在选举时做出错误选择。
我对户晨风这个人不熟悉,所以之前看他那个新西兰超市价格视频时并无任何固有印象。看完第一感觉是有点过于天朝 —— 生活除了吃,就没有别的追求了。旅游几天也远远无法真的了解一个国家。
平日中我有记账的习惯,所以对钱的去向过于清楚,以至于有时候觉得糊涂点比较好。就个人经验来说,不考虑其他来源的话,过去10年的工资增速几乎总是显著高于通胀,而今年是第一次落后 —— 我想一般岛民为了那20块钱减税投票时,可能没想到这解放的其实是雇主,而不是他们。如果年度工资调整比例是0%的话,通胀再低也跑不赢啊。
既然手上有这个数据,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以后在这个blog 存在的期间,会坚持每年大约这个时候回顾一下那些无法,或者很难逃避的生活成本每星期会花掉多少钱。 我不包括12月的原因也很简单,silly season 要么会突击花光预算,要么预算早已花光,哪个选项都不代表平日生活的成本。
生活
继去年一连串的天灾之后,今年的蔬果物价回稳,感觉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吃的这方面不刻意节约,也不无节制暴食。平时零食什么的管够,夏天各种好吃的草莓,蓝莓,樱桃之类的一样也不落下。虽然有时候钱包感觉有点疼,但本地是新西兰主要水果产区,有时候可以买到很便宜的应季水果。
疫情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减少了在超市的开销,更照顾个人经营的蔬果店或者农场店。平时自己也种点蔬菜。两者的目的都不是为了省钱—— 而是支持社区和获得一些超市里没有的蔬菜。
平日极少吃外卖或者餐馆,不是省钱,而是确实对外卖不太感兴趣,这里也没什么好吃的。Hawke’s Bay 的酒庄和fine dining 全国有名,特别是冬季旅游淡季时,能拿到相当划算的价格。不过这些不是生活必需品,就不计入了。
教育
价格是每星期50个小时。这也是一项无法逃避的支出,没什么太多可说的。国家党今年提出的早教退税和我无关 (不符资格)。 最近托儿所通知由于人手短缺,无法照顾小型人类的早饭,需要吃了之后再送去。
通讯
- 宽带 – $20.3 pw
- 手机 – $3.8 pw p.p.
Kogan 的出现使得流量的价格趋于合理。两个人在优惠时买一年180GB 那个套餐基本够用。只不过似乎不再有半价优惠,成本略有上升。
年中换了宽带服务商,800M网络的价格降到一个月$77。一年合同到期后应该会再换,拿新用户优惠。服务大同小异,每年重设下路由器每个月就可以节约$20以上,是一项相当值得的买卖。
交通
- 汽油 – $21 pw
- 公交 – $30 pw
- Rego / WOF / 保养 – $10 pw
按比例计算,今年上涨幅度最高的项目是公交 —— 理论上涨了200%。去年公交半价,单程价格$1。但国家党上台后去年的半价优惠结束,再度限制公交拨款使得价格上涨到$3,直接干掉了一星期$20的“减税”。
平日大约4星期左右一箱油。Flybuys 关闭导致的一个损失是,没有做问卷换汽油优惠的好事了。Rego 涨$50 块钱也还暂时没反应在价格里。
住
- 地税 – $104 pw
- 房屋保险 – $47 pw
我没有房贷,所以这个项目可能代表性不高。不过就地税来说,由于灾后重建需要,加上Havelock North 水污染事件后大规模投资供水基建,上涨压力巨大。今年的价格比去年贵了将近20%。
这两者都不是“减少浪费”能解决的问题。个人认为新西兰乡民去年选举时最失败的行为就是被挑动与毛利族裔间的矛盾。哪怕就是不喜欢毛利人,也应该坚持要求国家党迅速实行去掉了毛利影响的三水合并方案。现在这样拖着,全国各地面对的地税上涨真心是自找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偿还上一代人为了减税,在基建上欠下的债。
这项支出预计在未来几年还会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
房屋保险是房贷要求的必须项目,所以包括在内。维修没有算在内,因为理论上不是必需项目。
水电气
- 电费 – $20.1 pw
- 天然气费 – $19.7 pw
- 水费包含在地税中。
今年的冬天异常温暖 —— 虽然不刻意靠抖取暖,印象中今年冬天开暖气的次数不超过10次。但电和气两者的每日固定费用都面临着上涨压力,明年还会继续上升。
另外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是,电/气费和网费一样,每次调涨时找客服抗议是可以缓几个月的。
总结
今年维持生存必须的成本将近每星期$700,今年的最低工资是$23.15/h,假设一星期40小时,tax code M,一星期税后约$780 。也就是说加上房贷/房租,一个最低工资可能生存都不够。
乡民在进行对“福利狗” 的两分钟仇恨时,不一定意识到了依赖福利生活的人不仅是失业者。如果没有住房、早教,working for families等津贴,低收入者呆在这个国家是没有意义的,更无谓什么成家,以及喜闻乐见的繁衍后代了。这些福利本质上是补贴雇主和炒房客,而不是本人。
无论左右,现政府有一个合理,逻辑自洽的经济计划吗?答案是没有。